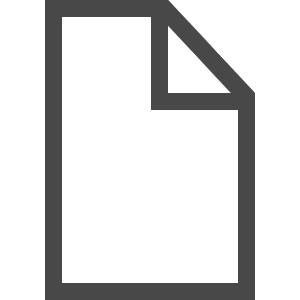2016年11月,我国在部分省市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监察法草案进行了审议,2018年3月20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监察法》。根据《监察法》第四条的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那么对职务犯罪的案件中,如何把调查取证工作与刑诉法进行证据上的衔接,这是刑事辩护律师必须要了解的课题。
目前《监察法》关于证据方面的规定,集中在第33条,笔者试着从第33条的规定,浅析监察法的证据审查以及与刑诉法的衔接。
监察法第33条:
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
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
关于证据能力问题
一直以来,关于证据能力,都会涉及到取证主体是否合法的问题,这也是刑事案件中对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一个前提条件。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不管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在取证的问题上,都是作为侦查机关来行使取证权,即使在过去的纪检部门收集的证据材料也是经过侦查程序进行转化(主要是言词证据的转化),才能够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
但我们知道,监察机关并不是侦查机关,而是政治机关,在《监察法》第18条中规定,监察机关的地位是“调查机关”,行使的是“调查权”而不是“侦查权”。那么监察机关行使的调查权收集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之后的刑事诉讼证据使用呢?如果能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与刑诉法会不会有衔接的法理障碍?
笔者认为,监察机关所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能作证据使用,也不存在衔接的法理障碍。主要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位阶相同,且《监察法》时间上靠后。《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都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在立法上处于同一位阶,都属于“基本法律”,而且,《监察法》制定的时间比《刑事诉讼法》靠后,即使对于同一关联问题作出不同的规定,也应当以《监察法》为准。
第二,《监察法》具有特殊性。相对于《刑事诉讼法》的普适性,《监察法》所适用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即使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也应当优先适用《监察法》。
第三,《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有明文规定,所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另外,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联合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以下简称《监察法释义》)一书中,对于33条第一款规定的释义就明确:本条是规范监察机关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的要求和标准,赋予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效力,是监察机关实现“法法衔接”的重要方面,这些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不需要刑事侦查机关再次履行取证手续。
证据的标准问题
既然监察机关所收集的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那么,是否意味着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都可以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呢?如何审查检察机关收集的证据并在刑事诉讼中进行衔接?笔者认为:
第一,适用我国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刑事证据的审查和运用相关的规定,具有可行性。《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的规定,只是明确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在之后的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只是一个证据准入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到证据的审查和运用,而且整部《监察法》条文都没有对证据如何审查和运用做出详细的规定。目前我国没有一部系统的证据法典,关于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审查和运用问题,大都分散于刑诉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上。既然《监察法》规定所收集的证据可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又没有详细规定如何审查和运用,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适用我国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刑事证据的审查和运用相关的规定,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监察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而且,在《监察法释义》一书中对这款的释义中,也明确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适用刑诉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
第三,如前所述,监察法与刑诉法具有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但并非不相容,只是优先适用监察法(其实在某些方面上监察法中规定的调查取证比刑诉法规定的更加严格,如《监察法》第41条)。如果监察法对某些问题没有规定但在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规定,毫无疑问适用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就是说,除了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其他能够约束审判机关对于证据审查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如果也对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做了规定,在监察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也应当适用这些规范性文件对证据进行审查。
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既然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能进入刑事诉讼中,而且对证据的审查和运用适用目前我国关于证据的审查标准,甚至《监察法》在某些证据方面提出更加规范和严格的要求,那么,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在思维方式上不存在障碍,也就是说,对于监察机关收集的非法证据同样可以启动排非程序,同样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
《监察法》第33条第三款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监察法释义》一书中对此款也作了详细的说明,并明确指出:经查证,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排除。
笔者提请需要注意的是:
《监察法》中关于“非法方法”与以往
稍有不同,其范围更广。
根据《监察法》第40条第二款的规定,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那么,可以得出《监察法》关于“非法方法”包括“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比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范围更广,程序更加严格,对监察机关提出更高的要求,有其进步性。
《监察法》并没有规定严禁刑讯逼供。
在《监察法》第40条的规定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监察法》都没有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只是在《监察法释义》表明。但严禁刑讯逼供几乎成为社会的共识,而且根据“举轻以明重”,严禁刑讯逼供是《监察法》应有之义。
《监察法》没有规定羁押、讯问场所、证人出庭
以及同步录音录像移送等问题。
《监察法》没有规定羁押、讯问场所、证人出庭以及同步录音录像移送等问题。笔者在这里特别重点谈下关于同步录音录像移送的问题。
其一,《监察法》关于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搜查、查封、扣押等程序工作。根据《监察法》第41条第二款的规定,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
其二,《监察法》里关于同步录音录像如何备查,没有明确规定。根据《监察法释义》对此款的释义:全程录音录像,目的是留存备查,但需要注意的是,监察机关对调查过程的录音录像不随案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认为需要调取与指控犯罪有关并且需要对证据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录音录像,可以同监察机关沟通协商后予以调取,所有因案件需要接触录音录像的人员,应当对录音录像的内容严格保密。从释义中似乎可以得出,检察机关可以调取相关录音录像,但目的只是备查,没有明确移送审判机关的问题。
其三,如果被告人提出线索材料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程序,而公诉机关却不能提供同步录音录像,难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如何解决?笔者认为,在目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下,尽管没有明确规定监察机关的同步录音录像移送审判机关,但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且监察机关、检察机关拒绝调取同步录音录像的情况下,法院也只能作出排除处理,否则不能体现“留存备查”的意义所在。
从《监察法》的条文来看,过于原则性,缺乏相关的实施细则,大体上比较粗疏。目前律师界对于《监察法》的诟病主要是第43条的留置措施,期限过长且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没有律师能够介入,似乎与现代文明相牴牾。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监察体系的成熟,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也必须解决。
文/郑世鹏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