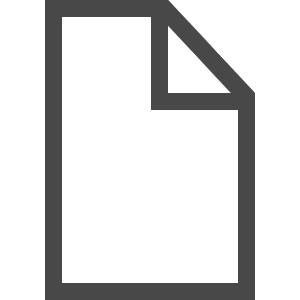曾几何时,我们把无罪辩护当作律师辩护的最高境界和刑事辩护皇冠上最亮丽的一颗明珠。很多知名的大律师也都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代理的无罪辩护案例当作职业生涯中最引以为豪的经历和巅峰之作,似乎只有成功地进行无罪辩护才能配得上大律师的荣耀。
大体而言,我国的无罪辩护有三种形态:第一种就是实体上的无罪辩护,也就是通过论证犯罪构成的某一个或者几个要件不成立来做无罪辩护。第二种是证据法上的无罪辩护。这种辩护也就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控方证据尚未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为由,主张根据疑罪从无的原理做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第三种是程序法上的无罪辩护。这种辩护主要通过论证侦查、起诉和审判活动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从而请求法庭排除非法证据,使案件定案证据不足,最后达到无罪辩护的效果,从本质上说,这种无罪辩护其实是程序辩护和证据辩护二者的结合。
证据法上的无罪辩护往往可以通过否定单个证据的证明力,使其不能转化为定案的根据,使证据的锁链发生断裂,从而达到无罪辩护的效果。
辩护律师如果从证据法角度做无罪辩护,应当着重研究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问题。我国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但这一证明标准却存在如下一些问题:第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是一个哲学标准,而不是法律标准,在实践中根本难以实现。第二,“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充其量只能算是诉讼证明的目的,而不能充当标准。在社会科学中,目标和标准具有不同的内涵。目标可以是暂时达不到的理想,但是标准必须具体,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在此,我无意介绍证明标准的学历争论,只想说明,作为辩护人,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利用现有的证明标准进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
任何价值的提出都不是为了价值而价值,都是为了解决和挑战实践中出现的反面现象,比如,提出正义是因为实践中有不正义,提出自由是因为实践中有奴役,提出平等是因为实践中有特权。所以,相对正义而言,人们对于非正义往往更为敏感,所以,“非正义”才是客观的、可操作的研究对象。幸福是无止境的,而苦难是有限度的,人们很容易在苦难和悲痛的问题上达到惊人的共识,但很难在幸福的标准上达成一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研究大量的非正义现象来研究正义本身。与其研究人权,不如研究侵权;与其研究正义,不如研究不正义。总之,研究价值应当将研究对象客观化,从价值的反面切入进行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同样的道理,我们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具有可操作性,但这一标准的反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却是有标准可循的,因为“证据不足”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人们在这一点上非常容易达成共识。概括起来,“证据不足”有以下几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第一,以孤证定案。任何证据不能自证为真,而要靠别的证据加以佐证和印证。孤证处于无法佐证的状态,因此无论该证据多么真实和稳定,都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定案。因此,以孤证定案肯定属于“证据不足”。
第二,“一对一”的案件。这种案件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强奸案件,第二种是受贿案件,第三种是伤害案件。前两类案件的发生都比较隐蔽,没有第三人在场,很难找到相互佐证的证据。而在多人参与的故意伤害案件中,究竟是谁造成了重伤或死亡的结果,往往是各执一词,根本无法查清,极为容易形成一部分证据证明有罪,而一部分证据又证明无罪的情况。有这样一起受贿案件,控方质控被告人的证据有:行贿人的证言,会计的证言,出租车司机搭载被告到小区的证言。而被告方举出的证据则有:被告人的妻子和保姆证明没有见过行贿人;搬家公司证明在控方指控的案发当天,被告家已经搬走半年有余;还有一个电话公司的装机工证明,他一直到当年的八月份才给被告家装电话,而证人则说之前给被告人家打了两个电话,明显存在重大矛盾。这个案件就是典型的“一对一”的情况,有罪和无罪两种可能性都无法排除,属于典型的“证据不足”。
第三,尽管有若干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但证明被告人犯罪行为过程的证据却是孤证。比如,虽然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被告有犯罪动机和犯罪时间,但证明犯罪过程的证据却只有被告人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辩护人可以运用“证据不足”来进行辩护。河南邯郸有一起故意杀人案,死者是被告人的妻子,有很多证据都对被告人不利。比如,被告人在外面有四个情妇,和妻子一直关系恶劣,甚至经常大打出手,还曾威胁妻子要与其离婚,但是,被告人前后六次供认的杀人手段和工具都不一致,律师就围绕着口供之间的矛盾展开辩护,其发言的核心就是几次口供交代的作案方式,无论哪一种都得不到其他证据的佐证,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因此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最终采纳了这一辩护意见。
第四,如果案件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或者不能排除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如意外事故或自杀),也应视为证据不足。在云南杜培武的案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一直没有引起各方的重视。辩护律师在进行二审辩护时当庭之处,现场勘验笔录明确记载,死者杜培武的妻子,衣服被扒光,胸部和阴部明显有被人猥亵过的痕迹,可杜培武作为死者的丈夫,会在基于仇恨杀害妻子之后还对她进行猥亵吗?这明显不合常理。这个关键证据引起了云南高院的高度重视,最好认定本案证据不足,存在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因而作为了留有余地的判决,改判死缓。
很多人认为,无罪辩护的成功必然应以无罪判决为标志,我认为这一要求过于苛刻,而且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前任院长肖扬在某次工作报告中的统计,五年来中国无罪判决总共只有一万多件,也就是说,在平均每年一百多万起刑事案件中,只有不超过三千件的无罪判决。当然,如果能说服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当然是刑事辩护的理想状态,可是面对如此之低的成功比例,我们恐怕还应该采取一种现实的态度,来维护被告人的权益,比如,促使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促使检察院撤回起诉;促使法院判处缓刑或“实报实销”的判决。因此,我们不能再狭隘的理解无罪辩护成功的标准,应当结合实际,从现实的角度来为被告人的权益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