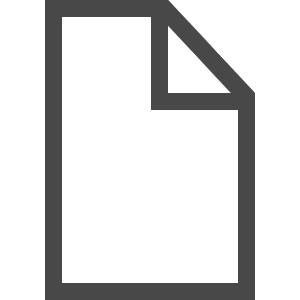2015年 9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正式对刘虎涉嫌诽谤罪、敲诈勒索罪以及寻衅滋事罪的案件做出存疑不起诉的决定。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决定在法律上的意义,仅意味着刘虎因证据的原因不够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但并不代表他没有任何违法事实。
刘虎案一直广受关注。本案伊始,刘虎就被某些人人为地打上了“因言获罪”、“因举报受打击报复”等标签,有人甚至认为这是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动用法律手段迫害媒体记者、限制言论的一种表现,从而对其前景十分担忧。
不过,窃以小人之心想一想,发点诛心之论的牢骚,也许这些人反而盼望着刘虎被判有罪,从而证明他们的谬论是多么的“伟大”。他们幻想着用极端的言论去挑战法律的权威。
因此,当刘虎被不起诉的消息传来,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某些人的想象和预测,在为检察机关带来一片赞赏之声的同时,也许我们还会听到几声酸酸的叹息。
就媒体披露的情况看,公安机关的侦查绝非空穴来风。检察机关对于刘虎案的办理过程是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认真审慎的。有人质疑检察机关对刘虎的“二次退补”是想置其于死地,然而结果却告诉世人,检察官们只想把案件的真相尽可能的查清楚,让各方都认可法律最终的裁决。
最终,我们看到在两次补充侦查之后,检察机关仍然认为该案的证据与事实达不到公诉条件,便依法对刘虎做出了存疑不起诉的决定。对于检察机关的办案过程,连刘虎自己都表示
“我很高兴检方能坚守法律底线,能独立思考,我对中国法律有信心。”
刘虎自己都有信心,那少数人为什么反而要疑神疑鬼呢?这起案件,刘虎算不得赢家,检察机关似乎也不算,真正的赢家是法律!法律以其特有的方式实现了它应有的权威!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司法机关办案的准则。刘虎案完全是法律说了算。法律的执行不会受权力的干预,同样不会受舆论的绑架。
刘虎案的办理结果体现了法律的公正,体现了检察机关对于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呵护与珍视。
答疑解惑
其一是对存疑不起诉的误解。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的不起诉主要有3种,一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以及没有犯罪事实发生或者虽然犯罪嫌疑人的行为造成危害后果,但从法律上并不构成犯罪的,应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称之为“法定不起诉”。
二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不起诉称之为“酌定不起诉”(又称“相对不起诉”)。
三是经过二次补充侦查检察机关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不起诉称为“存疑不起诉”。根据媒体报道看,刘虎案和吴永正、蔺文财案都属于第三种,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存疑不起诉”。也就是说,因为证明刘虎和吴永正、蔺文财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不符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条件,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这和不构成犯罪的“法定不起诉”是有着原则区别的。对于“存疑不起诉”的案件,如果发现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以再提起公诉。
其二是对罪与错的误解。
刑法是对公民行为的最低规范,触犯了刑法就是犯罪行为,就要处以刑罚。在刑法规范之外,还有社会管理法律规范,以及各种各类职业的规范和道德规范。所以,即便某一个行为不构成犯罪,也未必见得就值得歌颂,理所应当。曾经有过这样一件往事,一位被检察机关指控涉嫌受贿的市长,因为收受钱财后未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被法院宣告无罪。判决后,他要求检察院为他恢复名誉,要求党委给他官复原职。这个要求当然被拒绝了,因为他收受钱财的行为证据确凿,只是没有证据证明他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所以即便无罪,也是有错,应予以纪律处分。同样的道理,检察机关对刘虎案和吴永正、蔺文财案作出的“存疑不起诉”结论说明,他们只是不能认定为犯罪,而不是毫无过错。当然,检察机关只有权对是否起诉作出决定,而无权对公民的过错进行判断和处罚。这些过错有的需要通过其他规范来处理,有些过错则需要公民道德来判断。总之,我们对任何一个行为的判断必须实事求是。无罪并非无错,有错并非有罪。搞清楚罪与错的关系,才能准确判断一个行为的性质,既不把一般过错当犯罪处理,也不把犯罪降格为错误处理,更不是一旦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就意味着当事人完美无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