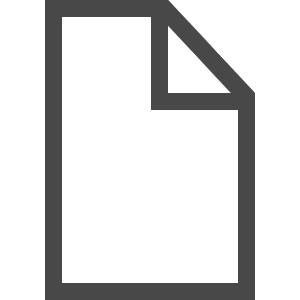看英美法律剧,经常看到在法庭上,控辩双方对于证人发问的激烈交锋,激烈交锋的过程中,突然间另一方向法庭提出异议:反对,诱导性发问。然后往往是法官对发问方予以制止。这就提出了本文的命题 ,谁在诱导证人?
1
什么是诱导性发问
什么是诱导性发问?在英美国家,对诱导性发问的定义,其内涵和外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即使是证据法学高度发达的美国,其《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也没有对何为诱导性发问进行定义,只是规定了允许和禁止诱导性发问的情形。通过对比相关对抗制庭审国家的规定,笔者归纳起来,所谓的诱导性发问,其内容主要是两点,第一是暗示证人如何回答(比较明显的是将问题的答案放进问题中予以暗示),第二是将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前提加以提问。
如《澳大利亚1995年证据法》就规定,所谓诱导性问题,一是直接或间接暗示了具体答案的问题,二是假设某事实的存在,而在程序中就该事实存在争议,并且在向该证人提出该证言之前证人还没有就该事实是否存在作证的问题。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笔者用下面的例子予以说明:
例一:案发当天早上你不在家,是不是?(暗示不在家)
例二:你走私的枪支有100支,是不是?(问题似乎问的是数量,但实际上对严格法律意义上有争议的“枪支”作为前提加以提问,也就说,这问题里包含的“枪支”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事实,但却作为问题的前提放进了问题中)
以上这两个例子都存在明显的诱导性发问。
2
我国司法关于诱导性发问的现状及原因
在我国的法律规范中并没有对诱导性发问进行定义,可以说我国目前并没有建立严格法律意义上的诱导性发问规则。在我国刑事法庭上,关于诱导性发问的问题,无论是控辩双方甚至是审判人员,都存在严重的诱导性发问问题。控辩审三方似乎也不关注诱导性发问,就是出现诱导性发问问题,控辩双方通常也无法及时提出异议,审判人员有时候也难以主动进行制止。
据笔者参与的庭审观察,对于我国目前司法存在严重诱导性发问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条粗疏、原则性难以操作。目前关于诱导性发问的法律规定,主要存在于最高法司法解释和最高检的诉讼规则里,但都是过于原则性的规定,而且,我国对证人的属性(控方证人/辩方证人)也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第二,诉讼参与人对诱导性发问的认识不足。第三,长期以来习惯于书面的辩护与审理,再加上我国证人出庭率过低,诉讼参与人都缺乏对证人当庭发问和质证的经验。
3
我国对诱导性发问的规范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只对法庭人证调查的程序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规定发问的程序和应当遵守的规则。最高法和最高检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但都过于粗疏,操作性不强。主要的法律规定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13条第2项规定:不得以诱导方式发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14条规定:控辩双方的讯问、发问方式不当或者内容与本案无关的,对方可以提出异议,申请审判长制止,审判长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对方未提出异议的,审判长也可以根据情况予以制止。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438条: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应当避免可能影响陈述或者证言客观真实的诱导性讯问、询问以及其他不当讯问、询问。
辩护人对被告人或者证人进行诱导性询问以及其他不当询问可能影响陈述或者证言的客观真实的,公诉人可以要求审判长制止或者要求对该项陈述或者证言不予采纳。
通过以上的对比,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最高法对诱导性发问的立场是明确的,就是任何形式的诱导性发问都是不允许的。
02
审判者对有争议的诱导性发问有最终的裁判权,但如果审判人员有诱导性发问(我国的刑事庭审中,因为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审判人员往往会对被告人就案件事实发问),如何救济,并没有明确规定。
03
对于诱导性发问,控辩审三方如果都没有异议,如何处理?换句话说,最高法的规定并没有强加于诉讼参与人反对、制止的义务(不是“应当”而是“可以”),如何执行第213条的规定是个问题。
04
最高检的规则是并不完全禁止诱导性发问,只是禁止违背客观真实的诱导性发问,与最高法的规定稍有不同,但操作性不强。更何况何为客观真实,如何判断,以及在以庭审为中心的趋势下,公诉人在对于诱导性发问的诉讼行为只有建议权,审判人员更多只会执行最高法的规定来主持庭审的程序。
另外,《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20、21条,以及最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深圳市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实施规程(试行)》第74、75条都没有超出最高法的司法解释的范畴,故不再另外阐述。
诱导性发问是在刑事法庭上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如何应对诱导性发问的问题,规范庭审,使“审判成为一个高度技巧化的竞技场”,还有待细化相关的证据规则,完善合理可行的证据体系。
文/郑世鹏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