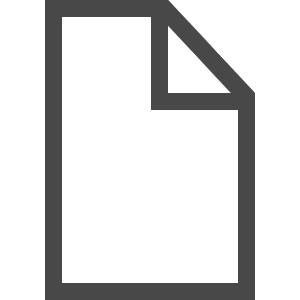国家赔偿记:这样的制度,为谁而设?
最近办了几个国家赔偿的案件,申请国家赔偿的,都是年轻人。被称为新一代农民工的他们,游走在这个城市的边缘,似乎格格不入。他们不曾想到,因为各种偶然,会与所谓犯罪,扯上不清不楚的关系。虽然最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不起诉,然而,于他们而言,其中种种经历,不啻午夜梦回。
我们提出赔礼道歉,正式的法律文书只字未提,不知道是他们认为太过习以为常还是麻木不仁?又或者认为当事人从国家赔偿中拿到的几万元就足以平复他们所受到的伤害?
5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最新的国家赔偿标准,每天258.89元,比之前的标准提高了16.59元。我们国家没有惩罚性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所以,计算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少得可怜。有人算过,错误拘留错误逮捕,关押一年,得到的赔偿在深圳购买不了两平米的房子。相比那些高官权贵贪污受贿,其中差别,何止云泥。我们的主流价值观,洋洋洒洒几十个词语,关键时刻,连平等二字也要打上双引号。虽然《国家赔偿法》不乏“追偿”和“追责”条款,但这些年来,并没有在相关公务人员中起到监督和警示作用,而所有的赔偿,最后还是纳税人买单。
泛刑主义盛行的今天,不知道这样的制度,为谁而设?
在这几个年轻人中,有一个在他被关看守所的日子里,父亲离世,生前不能尽孝,出来后,黄土一坯,阴阳两隔。有一个,妻子因承受不了压力,抛家离去,出来后,妻离子散。有一个,被关之前是工厂里的经理,出来后,被贴上各种罪犯标签,工作不好找,家人不接纳,举目无亲。有一个,我和他走进检察院,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在看守所学会的那套还没有完全改过来。有一个,从福建坐高铁过来,说谁都不相信,公安也不敢相信,当初接到公安电话说过去调查,就从工厂了请了三个小时的假,结果去了派出所,一去就被关了八个月,一切都没有准备,一切都没人知道,大家都以为他失踪了。
想起余华小说《活着》,想起《活着》里面那个叫福贵的老人,穷困之中福贵因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凤霞不幸变成了聋哑人,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一幕幕渐次上演。
剧中事,影中人,小说与现实,惊人的相似,不知这样的制度,为谁而设?
记得曾看过一部关于上访的纪录片,发现电视台播出的感人故事也是假的,故事里的女孩真有其人却非其事,但电视观众只知道被故事感动,跟着流泪。在今天的现实中,因为缺乏可以验证的渠道,是真是假变得没有所谓。小说与人生可以互换,还有什么可以相信?没有,只能相信一件事:活着,就是。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如果自由可以用金钱来量化,那么每天只值258.89元。似乎风牛马不相及,背后都是尊严——是一个人的尊严和一个民族的尊严。本来这是人之所本国之所系,引起嘘唏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里早已佚失的尊严,礼失求诸野,当一介市民说出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当一个民族渴望对人性的重视,其实我们并没有做得更好。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这样的制度,为谁而设。
文/郑世鹏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