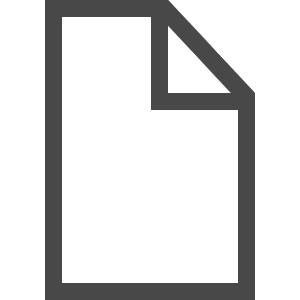有人研究中国已经提前进入诉讼社会了(详见张文显教授的研究),虽然我们还没有进入法治社会。
十多年来,我们评选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致力于通过个案促进法治。从每年当选的十大中国影响性诉讼来看,十有六七是刑事案件,最大影响的案件主要是刑事或与刑事相关的案件,尤其那些杀人、强奸背景的冤狱。
古代中国亦是如此,我们不是自秦朝之后一直续演着孟姜女哭长城,铁面包公等冤狱平反的故事吗?为什么几千年来,在建设法治中国的今天,我们的正义观还停留在冤案非冤案的层面?冤狱是诉讼社会的悲哀,是建设法治中国的悲哀。我们向无罪辩护的成功致敬,向所有为冤案平反做出努力的人致敬,但同时我们也要反思冤案产生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努力铲除制造冤狱的土壤。
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不受制约的权力,以及人们对权力的顶礼膜拜,奴性文化是滋生冤狱的制度和文化土壤。此种制度文化环境下的正义观,并非以权力制约权力,而是延续不断重复着“制造冤狱—获得平反—感恩鸣谢”的模式。
诉讼社会,建设法治中国的顶层设计,亟需尽早走出冤狱正义观的窠臼,落实人民主权原则,守护共和国理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制度,最高层面就是宪法,就是那些基本的法治原则。
什么时候我们的十大案件,不再是以刑事案件和冤狱为主?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出现马伯里诉麦迪孙案那样确认行政权与司法权之争的案件?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出现布朗诉教育局案那样判决隔离并非平那样深远意义的平等权案件?什么时候我们我们能够出现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那样厘清言论自由边界的案件?
相信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共同感受法治春天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