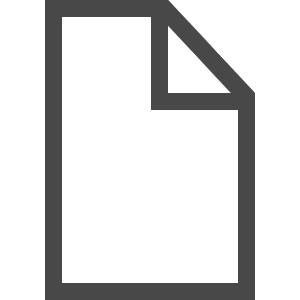近年来法律对网络言论的规制越来越严格,但实务中对网络诽谤的界定却并不明确,模糊不清的言论边界,导致网民动辄触犯法律法规。实践中,公安机关常常用寻衅滋事、诽谤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某种程度过激或传播不实的言论进行处罚。而在律师界,去年就有两宗影响颇大的关于律师之间网络诽谤的刑事自诉,成为网络诽谤在律师界的盛事。净化网络空间,规制不文明的言论固然是好,但若言论的边界模糊不清,难免会扩大处罚的打击面,造成言论空间的进一步收缩,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蒋惠玲主编的《网络刑事司法热点问题研究》一书,对网络诽谤作出了详实的论述。摘录书中一段文字如下:
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长期深入调研、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明确规定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的认定及处罚问题,为司法机关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此类犯罪,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此后,“两高一部”又先后下发了《关于严格依法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违法犯罪案件的意见》《关于严格依法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违法犯罪案件的意见(二)》(以下简称为《意见》),进一步统一了认识,明确了适用法律标准,适应了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解释》出台后,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了一批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如北京秦志晖诽谤、寻衅滋事案、北京尔玛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杨秀宇非法经营案、云南董如彬非法经营、寻衅滋事案、上海傅学胜诽谤案等,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实践证明,《解释》的出台是完全必要的、及时的、有效的,对于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网络健康发展,促进立法进一步完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解释》及其配套的两个《意见》,是当前打击治理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的主要法律规范。
从以上书中的话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一,“两高一部”先后下发了《关于严格依法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违法犯罪案件的意见》、《关于严格依法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违法犯罪案件的意见(二)》(以下简称为《意见》)明确了适用法律标准,适应了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二,两个《意见》是当前打击治理网络谣言的主要法律规范。也就是说,两个《意见》已经在实践中适用。
笔者注意到,此书是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且书中也有最高人民法院副庭长撰文,应当能代表官方的观点和态度。然而此书虽然对网络诽谤有诸多阐述,但书中并没有收录两个《意见》的文本。笔者也分别搜索两高一部的官方平台,也没有看到此两个《意见》的法律文本。也就说是,此两个《意见》的文本并没有对社会公众公开。
通过搜索平台,在新兴县公安局2015年9月9日的官网中,搜索到关于印发《广东省公安机关办理网上诽谤案件执法指引》的通知(以下简称《执法指引》),此《执法指引》的法律依据就有两个《意见》。另外,在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2月4日的官网上,有法院要闻《濮阳县法院学习贯彻“9.16”打击网络诽谤等犯罪司法指导意见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全文摘录如下:
为贯彻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制定印发的《关于严格依法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违法犯罪案件的意见(二)》精神,12月2日下午,濮阳县法院组织全体干警在二楼会议室观看学习“9.16”打击网络诽谤等犯罪司法指导意见的电视电话会议,在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随即召开院务会,就如何贯彻落实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行了安排部署。
一是组织干警领会会议精神。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该院向一线办案法官下发《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严格依法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违法犯罪的意见二》全文,为法官司法审判提供重要参考。全院干警以部门为单位,利用每周五下午时间集中学习领会文件精神,贯彻习总书记“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重要指示,院领导班子在党组会议室集中进行专题学习。
二是举行内部交流专业研讨会。为更好在司法审判中运用好《解释》、更好贯彻落实《意见二》,该院要求组织由全院刑事审判工作人员及主管领导参加的专题实务交流会,就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适用问题进行交流,尤其对此次《意见二》中认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非法经营犯罪中的认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三是强化协作形成合作机制。积极邀请律师、公安、检察院等工作人员举行联席会议,就办理案件中的适用问题进行定期不定期交流,畅通沟通渠道,廓清模糊认识,确保执法、司法尺度的合法合理性,增强工作默契,全力确保案件得到公正裁判。
从以上搜索得出的信息是:一、两个《意见》成为执法细化的法律依据;二、公安局、法院等部门系统学习两个《意见》,并在实际中运用两个《意见》认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非法经营等违法犯罪活动,裁决案件。
至此,非常明确的是,两个《意见》在法律实务中实际运用,但并不对社会公众公开。
2018年8月,笔者申请信息公开此两个《意见》,并于当月得到了回复。公安部以此两个《意见》属于刑事司法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范围不予以公开。因笔者至今未曾看过两个《意见》的文本,故无法对两个《意见》的内容作出任何评价,但就公安部的回复,作以下猜测,或者是对此回复的回应。
第一,从两个《意见》的制定的主体来看,属于“两高一部”,向公安部申请信息公开,本身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
第二,从两个《意见》的标题来看,包含“违法”和“犯罪”的信息,也就是说关于“违法”和“犯罪”的网络诽谤等活动都应当适用此两个《意见》,那么,把“违法”纳入刑事司法信息,则有以偏概全之嫌;
第三,从以上笔者的搜索内容来看,《执法指引》的法律依据之一就是两个《意见》,且认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非法经营等违法犯罪活动中,违法程度较轻且不构成犯罪的往往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拘留,并非一定就属于刑事司法,而此回复,混淆执法与司法的界限。
第四,如果两个《意见》如回复所说,属于刑事司法信息,那么会带来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作为刑事司法信息的法律文本,却没有向社会公众公开。换句话说,一不小心,就入罪了。
法的公开,本身就是法治国家最基本的要求。法的发展过程,也是从不公开到公开的一个过程。古代的郑铸刑书、晋铸刑鼎,就是法的成文化进程。法的指引性要求人民对自己的行为有某种预测,而不公开的法将使人民无法按照法的要求预测自己的行为,从而无法保障自由,古代的“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就是法的不公开,人民无法得知法如何规定,从而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是否触犯法律。如果一种行为,有的人可以做,有人的不能做,昨天可以做,明天不可以做,甲地可以做,乙地不可以做,这种没有预测可能性的法律制度,完全背离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和实质要求,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
曾听一法官关于毒品案件的讲座,主要是关于毒品案件怎么细化裁判的内部规定(不对社会公开),旁边的律师奋笔疾书,速记、录音,手忙脚乱,台上的法官,真理在我手,一览众山小。原来,很多时候在法庭上,律师辩律师的,法官判法官的,一别两宽,各不相侵。
法在内部运用且对社会公众普遍适用但不公开的情况下,还会导致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司法界一直诟病的问题:判决书不说理。在目前中国司法普遍适用的演绎法,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到结论的三段论,因为作为大前提的法律无法对外明示(不公开),只能顾左右而言他,甚至往往忽略不提,说理的成分就显得单薄而贫瘠,人民对司法的信任、法治的信仰,往往就大打折扣。
文/郑世鹏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