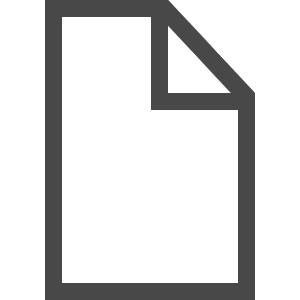去年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遇到两个事情:
一个是在看守所会见我的一个当事人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所在的仓里面所有的人一个月都买不了东西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仓里面有人打架,而里面有规定,如果发生打架的,所在的仓里所有的人一个月内都不能消费。
另外一个事情一个涉黑案件,辩护人在侦查阶段长期不能会见,有关部门给我的回复就是,涉嫌重大贿赂(监察委成立前)。后来到审查起诉阶段,总算见上了,也阅了卷。通过阅卷发现,所谓的涉嫌重大贿赂,与我的当事人没有任何关联性。
这两个事情虽然毫无关联,但它们内在都似乎指向了一个命题:一个人能否因为他人的不法行为而受到处罚?或者说,一个人能否因为他人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
在提出这个命题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无疑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连坐。
连坐指本人未实施犯罪行为,但因与犯罪者有某种关系而受牵连入罪。连坐起源甚早,夏、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连坐制度。商鞅变法时,立连坐之法。如《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司马贞索隐:“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
关于族刑连坐制的废除,是清末法律变革运动的成果之一。在当时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的努力并大力倡导下,清廷终于在1905年正式宣布废除连作制。至此,族刑连坐制度正式在法律上被废止了。不过,这种废止是有极大保留的。1905年之后,从各种法律文件中,依然可以看到连坐时隐时现。
如果从工具论的角度来看,通过连坐式的管理,对管理者来说,确实是个好方法,高效而便捷。但按照现代法律原则,一个人只能就其所犯的过错负责,这叫“责任自负”。所以在刑法上,严格按照“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来规制人的行为,追究人的责任。
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两个案例。案例一中,仅仅因为关在同一个仓这么一个同仓关系,就被禁止消费。试问,同仓的关系,是否有义务去制止另外两个人的打架?如果有义务,这种义务的正当性何在?否则连责任都谈不上。案例二中,一个与重大贿赂毫无任何关联性的人(通过阅卷可知),是否能因为办案单位办理案件的便捷需要而限制辩护人会见?
目前网络上关于类似这方面的报道不少,如去年的河南信阳罗山县“打击盗窃民航旅客财物犯罪专项治理行动办公室”,针对当地4名偷盗嫌疑人,发出一则劝返告知书称,“必要时将其父母、兄弟姐妹、儿子儿媳、女儿女婿曝光”“全部拉入诚信系统,限制出行,株连三代人”“在其家门口、村口悬挂‘飞天大盗之家’”牌子等。广东揭阳惠来县鳌江镇的10户家庭,房屋外墙上被当地政府人员用漆喷上了“涉毒家庭”的字样。
方法层出不穷,连坐殊途同归。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在中国,子女犯罪,父亲是受处罚的,秘鲁也有同样的习惯,这个习惯是从专制思想产生出来的。仅因为是犯罪人的亲属而受到处罚,本身就是对人性的一种否定。其后果,则使得有责任的人害怕法律,没有责任的人,无时不处于恐慌之中。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周围我们身边的人因为不法行为而连坐了自己,我们因他人的不法行为而受到处罚。
恪守任何人不因他人的不法行为受处罚,避免打击扩大化,是严格落实个人责任主义的要求,也是和谐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文/郑世鹏律师